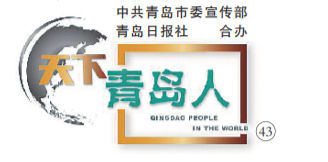
這位青島籍藝術(shù)家歸來(lái),不僅帶來(lái)他的最新水墨巨作《開(kāi)國(guó)大典》,還有關(guān)于中國(guó)畫(huà)創(chuàng)作新的觀念與視野——
趙建成:藝術(shù)的本質(zhì)是時(shí)代的胎記與投影

趙建成的水墨巨作《開(kāi)國(guó)大典》
中秋過(guò)后,趙建成攜他歷時(shí)一年半完成的最新水墨巨作《開(kāi)國(guó)大典》從北京回到家鄉(xiāng)青島。這幅原作入藏中國(guó)共產(chǎn)黨歷史展覽館的巨幅水墨人物畫(huà),長(zhǎng)12米、高4.2米,作為慶祝中國(guó)共產(chǎn)黨成立100周年國(guó)家重大歷史題材美術(shù)工程的點(diǎn)睛之作,如今量身復(fù)刻,懸掛于上合青島峰會(huì)的舉辦場(chǎng)館——青島國(guó)際會(huì)議中心,仿佛學(xué)成歸來(lái)的孩子熱切分享給他所熱愛(ài)的故土鄉(xiāng)親的一枚彰顯學(xué)業(yè)成果與實(shí)績(jī)的勛章。而此時(shí),距離這位年逾古稀的著名青島籍藝術(shù)家離鄉(xiāng)進(jìn)京,已過(guò)去了16個(gè)年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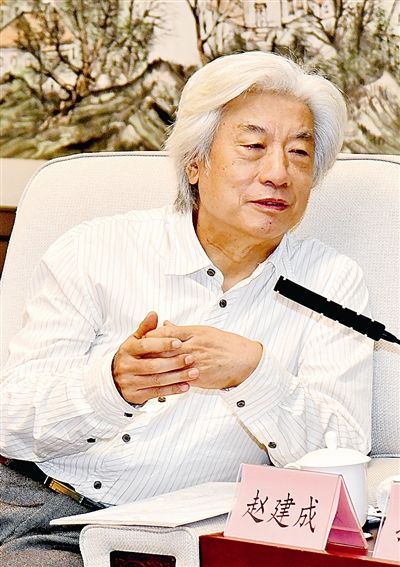
趙建成 王雷 攝
自上世紀(jì)80年代直至2005年離開(kāi)青島,趙建成都是創(chuàng)造本土美術(shù)現(xiàn)象不可或缺的領(lǐng)軍者:作為山東省創(chuàng)新水墨人物畫(huà)的奠基人,20年間,他連續(xù)在五屆全國(guó)美展中收獲大獎(jiǎng),于整個(gè)中國(guó)美術(shù)界都是佼佼者;他任青島市美協(xié)主席之時(shí),“強(qiáng)勢(shì)”之名已然在外,青島美術(shù)創(chuàng)作于第十屆全國(guó)美展上的現(xiàn)象級(jí)巔峰,便在其任期內(nèi)成就:水彩畫(huà)、中國(guó)畫(huà)、油畫(huà)、版畫(huà)全面“開(kāi)花”,斬獲一金二銀五銅,獲獎(jiǎng)總數(shù)占據(jù)當(dāng)年全省的半壁江山……風(fēng)生水起之際,年過(guò)半百的趙建成收到當(dāng)時(shí)文化部的一紙調(diào)令,離青入京,去到中國(guó)藝術(shù)研究院,專(zhuān)注于專(zhuān)業(yè)領(lǐng)域的學(xué)術(shù)探究,并自此開(kāi)啟個(gè)人創(chuàng)作生涯的全新之境。
2007年參與國(guó)家重大歷史題材美術(shù)工程,創(chuàng)作《國(guó)共合作——1924·廣州》;2012年創(chuàng)作中華文明歷史題材美術(shù)創(chuàng)作工程作品《民族會(huì)盟——七溪會(huì)閱圖》;2018年為“一帶一路”國(guó)際美術(shù)工程創(chuàng)作《康熙西征》……其中,2012年為北京市精心研磨推出的重大歷史題材作品《換了人間——1949·北京》。一系列影響全國(guó)、記錄時(shí)代的重大題材巨制,讓趙建成在純粹的學(xué)術(shù)征途上再上層樓,躍身中國(guó)畫(huà)的當(dāng)代大家。
在中國(guó)美術(shù)界獨(dú)樹(shù)一幟的歷史畫(huà)敘事中,趙建成另辟蹊徑。而面對(duì)傳統(tǒng)水墨的傳承與創(chuàng)新、人們對(duì)當(dāng)代性表達(dá)的質(zhì)疑與困惑、中國(guó)歷史畫(huà)創(chuàng)作傳統(tǒng)之于藝術(shù)家個(gè)性表達(dá)的限制,他總能夠在看似不可調(diào)和的矛盾中蹚出一條唯我獨(dú)行的路徑來(lái)。年深日久,技法與經(jīng)驗(yàn)持續(xù)累積,藝術(shù)家的創(chuàng)作不但沒(méi)有隨年紀(jì)的增長(zhǎng)而僵化老朽,反而愈發(fā)滿(mǎn)溢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的熱情與歡欣。
這位共和國(guó)的同齡藝術(shù)家告訴記者,藝術(shù)原本“應(yīng)逢其時(shí)”,因?yàn)樗囆g(shù)是對(duì)于時(shí)代的創(chuàng)造性表達(dá),它的本質(zhì)正是時(shí)代的胎記與投影,沒(méi)有創(chuàng)造不能稱(chēng)其為藝術(shù);不與時(shí)代同行的藝術(shù),則不具有任何存在的價(jià)值。
在限定中實(shí)現(xiàn)豐富立體的關(guān)照
記者:《開(kāi)國(guó)大典》的創(chuàng)作歷時(shí)一年半,為這次創(chuàng)作您具體做了哪些準(zhǔn)備?
趙建成:我是在2019年下半年,接到慶祝中國(guó)共產(chǎn)黨成立100周年美術(shù)創(chuàng)作工程組委會(huì)交給我的這一創(chuàng)作任務(wù)的。應(yīng)當(dāng)說(shuō),以中國(guó)畫(huà)這一民族藝術(shù)形式講述開(kāi)國(guó)大典,是文化自信在藝術(shù)門(mén)類(lèi)上的具體體現(xiàn),其國(guó)家意義、文化意義重大。但是要在一年多時(shí)間里完成它,無(wú)疑是相當(dāng)嚴(yán)峻的考驗(yàn)。

為了繪制《開(kāi)國(guó)大典》,趙建成畫(huà)了近百幅人物素描。
在此之前,我曾歷時(shí)5年,在2012年完成了為北京重大歷史題材創(chuàng)作組創(chuàng)作的《換了人間——1949·北京》,當(dāng)時(shí)做了大量案頭工作,查閱近3萬(wàn)張歷史照片,還有大量相關(guān)文獻(xiàn)史料,畫(huà)了近百幅人物素描,為尋求貼切的繪畫(huà)語(yǔ)言和表現(xiàn)形式作了大量實(shí)驗(yàn)性探索。這些積累為2021年《開(kāi)國(guó)大典》的創(chuàng)作完成做了重要鋪墊。這幅作品之所以能在一年半時(shí)間內(nèi)、而且是疫情期間完成,多虧了這些前期積累。
記者:您是在圖片和影像資料中選擇畫(huà)作所要表現(xiàn)的人物形象和具體場(chǎng)景的嗎?現(xiàn)在回想,創(chuàng)作中遇到的最具體的困難是什么?
趙建成:歷史畫(huà)的創(chuàng)作,如果一味根據(jù)照片影像來(lái)臨摹,一定是死的。照片只是歷史的依據(jù)和參考,關(guān)鍵在于如何塑造歷史人物的形象與性格,準(zhǔn)確捕捉他在歷史情境中的心理、姿態(tài)、表情。對(duì)每一個(gè)人物,我力求綜合他們的歷史功績(jī)、共和國(guó)時(shí)期的作為、命運(yùn)的結(jié)局等多方面因素,進(jìn)行立體地關(guān)照,塑造出他們的精神世界,達(dá)到骨子里的“像”。但是要真正做到這一點(diǎn),并非易事。
專(zhuān)家為我的這次創(chuàng)作確定了三個(gè)原則:一是必須是開(kāi)國(guó)大典的具體儀式場(chǎng)景;二是必須有天安門(mén)的場(chǎng)景;三是尊重歷史事實(shí),未出席者不能入畫(huà)。本來(lái)中央人民政府一共有63位開(kāi)國(guó)元?jiǎng)祝罱K依據(jù)真實(shí)場(chǎng)景入畫(huà)的是52位。比較湊巧的是,2019年一部前蘇聯(lián)拍攝的關(guān)于新中國(guó)開(kāi)國(guó)大典的彩色紀(jì)錄片公映,而在此之前只有中央新聞紀(jì)錄電影制片廠拍攝的一段不清晰的黑白片,那部彩色紀(jì)錄片我觀看了近百遍,對(duì)開(kāi)國(guó)大典的時(shí)代背景和歷史語(yǔ)境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影片中,天安門(mén)城樓上的人物都自然地站立,大家的胳膊都撐在欄桿上,大典現(xiàn)場(chǎng)是一個(gè)人頭攢動(dòng)、摩肩接踵的場(chǎng)景。創(chuàng)作的難度在于,你不能夠照搬原先的場(chǎng)景,其中的限定很多。要在限制中體現(xiàn)出豐富,還要出新、出奇,很難。我的創(chuàng)作數(shù)易其稿,一上來(lái)就遇到很多困難未能解決,始終不能確定下來(lái)的,是如何以52個(gè)人物為主體來(lái)進(jìn)行整體的構(gòu)圖與立意布局。
記者:有關(guān)“開(kāi)國(guó)大典”的主題創(chuàng)作,前有油畫(huà)大師董希文的經(jīng)典之作《開(kāi)國(guó)大典》,中國(guó)畫(huà)則有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唐勇力教授的工筆《新中國(guó)誕生》。有沒(méi)有從他們那里汲取些許經(jīng)驗(yàn)和靈感?您的創(chuàng)作又如何展現(xiàn)不同的風(fēng)格特質(zhì)?
趙建成:董希文先生的《開(kāi)國(guó)大典》,是空間大于主體物象的宏觀架構(gòu),景大于人;唐勇力的工筆重彩推陳出新,融合西畫(huà)的素描寫(xiě)實(shí)造型,又吸收敦煌壁畫(huà)的裝飾元素。最初構(gòu)思時(shí)一度很茫然,還是延安時(shí)期的一幅老照片激發(fā)了我的靈感。在那張照片上,毛主席一行人站在農(nóng)村的土臺(tái)子上,人與臺(tái)渾然一體,拍攝視角從下往上看,只見(jiàn)身軀,看不到腳,而崇高嚴(yán)肅的氣氛并沒(méi)有減少。這個(gè)“臺(tái)”的功能寓意讓我興奮不已。
將決定中國(guó)歷史進(jìn)程的人物群像,雕塑般地立于漢白玉雕欄的臺(tái)階上,臺(tái)階演化為一個(gè)不可撼動(dòng)的基座,在其上“雕砌”出新中國(guó)的希望。開(kāi)國(guó)元?jiǎng)咨砩戏e蓄的博大、深沉、厚樸、凝重的情緒,折射出來(lái)的就是中華民族的精神與魂魄;他們胸前的紅布條,則是象征民族精神的火炬、戰(zhàn)火硝煙中屹立不倒的紅旗……人是一切藝術(shù)的重大命題,正是這一理念,決定了我的創(chuàng)作要以人為主體、天安門(mén)元素為輔,這些構(gòu)成了《開(kāi)國(guó)大典》的基本圖式架構(gòu)。

趙建成創(chuàng)作繪制《開(kāi)國(guó)大典》。(資料圖片)
《開(kāi)國(guó)大典》的創(chuàng)作語(yǔ)言是全因素的,它有著明確的時(shí)代烙印,造型、筆墨與色彩的結(jié)構(gòu)。黑白灰、黃色、紅色的交織使畫(huà)面熠熠生輝,一派光明。這里面有我明確的藝術(shù)觀念和思想,整個(gè)創(chuàng)作藝術(shù)形式的呈現(xiàn),都帶有強(qiáng)烈的獨(dú)創(chuàng)性和個(gè)人色彩。
藝術(shù)的真實(shí)比歷史的真實(shí)更深刻
記者:十余年來(lái)多次參與重大歷史題材創(chuàng)作,您如何看待中國(guó)的歷史畫(huà)創(chuàng)作傳統(tǒng)?在當(dāng)前所處時(shí)代,我們是否還需要?dú)v史畫(huà)?
趙建成:歷史畫(huà)創(chuàng)作,我們應(yīng)該這樣來(lái)認(rèn)識(shí):從世界文化的角度來(lái)看,它的確已成為過(guò)去時(shí),但在新中國(guó),歷史畫(huà)創(chuàng)作一直伴隨著國(guó)家的歷史命運(yùn)前行,它存在的意義就在于為我們的國(guó)家和民族留下視覺(jué)的記憶,建立國(guó)家藝術(shù)形象,是文化強(qiáng)國(guó)的視覺(jué)表達(dá),是在為一個(gè)國(guó)家和民族樹(shù)碑立傳,建構(gòu)獨(dú)屬于它的民族史詩(shī)。
就藝術(shù)本身的發(fā)展而言,中國(guó)歷史畫(huà)的創(chuàng)作,在其發(fā)展進(jìn)程中,也大量吸收了世界繪畫(huà)元素,加之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繪畫(huà)的繼承,形成了新的歷史畫(huà)樣式,這是對(duì)于時(shí)代的貢獻(xiàn)。而歷史畫(huà)對(duì)于創(chuàng)作者也有著極高要求:要有好的基本功,有完整的知識(shí)結(jié)構(gòu)和歷史學(xué)修養(yǎng)。以《開(kāi)國(guó)大典》的創(chuàng)作為例,人物從外在到內(nèi)在的塑造,都很有難度,除了具備專(zhuān)業(yè)歷史學(xué)的修養(yǎng),還要有大架構(gòu)、大畫(huà)幅的主題性繪畫(huà)創(chuàng)作能力,以及很高程度的寫(xiě)實(shí)能力。而這種寫(xiě)實(shí)既繼承了中國(guó)傳統(tǒng),又汲取了西方繪畫(huà)的價(jià)值,形成了中國(guó)畫(huà)的變革。從上世紀(jì)80年代初開(kāi)始,由古典形態(tài)向現(xiàn)代形態(tài)轉(zhuǎn)化的中國(guó)傳統(tǒng)繪畫(huà)的學(xué)術(shù)變革,就一直在發(fā)生。
我曾說(shuō)過(guò),國(guó)家歷次重大歷史題材的創(chuàng)作,都催化了中國(guó)畫(huà)全因素語(yǔ)言的發(fā)展形成,中國(guó)畫(huà)已經(jīng)不僅僅是工筆與寫(xiě)意的傳統(tǒng)類(lèi)別劃分,而是融匯了中西繪畫(huà)多種表現(xiàn)方式和元素。實(shí)際上,正是重大歷史題材的創(chuàng)作推動(dòng)了中國(guó)畫(huà)的歷史變革與學(xué)術(shù)創(chuàng)新,改變了中國(guó)畫(huà)的實(shí)踐形態(tài)和樣式面貌。
記者:您是否擔(dān)心歷史畫(huà)創(chuàng)作會(huì)因?yàn)槠錃v史的真實(shí)性而對(duì)藝術(shù)家的創(chuàng)造表達(dá)造成某種束縛和限制?
趙建成:在這一點(diǎn)上我比較認(rèn)同浪漫主義畫(huà)派的代表人物德拉克洛瓦所說(shuō)的:歷史畫(huà)創(chuàng)作實(shí)際上是畫(huà)家依據(jù)歷史的文本,像導(dǎo)演一樣進(jìn)行一次再創(chuàng)造。歷史的真實(shí)和藝術(shù)的真實(shí),本質(zhì)上是不同的,但藝術(shù)的真實(shí)把歷史的真實(shí)挖掘演繹得更加深刻,也更貼近人的心靈。人們?cè)谶@一再創(chuàng)造中感受到的真實(shí)與深刻,不是歷史的真實(shí),卻更加動(dòng)人。恰恰是歷史的真實(shí)文本和題材為圖像與風(fēng)格的塑造提供了更廣闊的可能性,歷史上那些偉大的歷史畫(huà)畫(huà)家已經(jīng)向我們說(shuō)明,他們是如何以美學(xué)意義上的真實(shí)喚醒了歷史的真實(shí)。
藝術(shù)必須是與時(shí)代并行的創(chuàng)造
記者:您在2005年離開(kāi)青島,當(dāng)時(shí)來(lái)看,您在青島的美術(shù)事業(yè)發(fā)展正漸入佳境,而且那時(shí)您已經(jīng)55歲了,是出于怎樣的決心,才讓您跨出“背井離鄉(xiāng)”這一步?
趙建成:文化部調(diào)我進(jìn)京,是國(guó)家從全國(guó)向北京選拔輸送人才,的確,當(dāng)時(shí)我已經(jīng)55歲了,卡在年齡的上限,從世俗的角度來(lái)講,許多人都不太理解。而我的想法是,一直以來(lái)我都有自己的學(xué)術(shù)追求,到北京去做一個(gè)純粹的畫(huà)家,符合我的個(gè)人期許。在北京,在更為深厚的文化土壤里扎根,有更高的創(chuàng)作交流平臺(tái),或許能夠做出更多的貢獻(xiàn)。實(shí)際的情形也正是如此,在北京16年,我的整個(gè)藝術(shù)觀念、繪畫(huà)樣式風(fēng)格都發(fā)生了很大變化。
記者:中國(guó)畫(huà)或者說(shuō)水墨人物,當(dāng)下尤其面臨著新的挑戰(zhàn)和考驗(yàn),我們常常提到一個(gè)詞——守正創(chuàng)新,您個(gè)人如何看待中國(guó)畫(huà)的發(fā)展前景和方向?
趙建成:在北京參加各種研討活動(dòng),大多是關(guān)于中國(guó)畫(huà)當(dāng)下的發(fā)展路徑的。我的認(rèn)識(shí)是,在全球化背景里,中國(guó)文化的生態(tài)發(fā)生了變化,中國(guó)畫(huà)是中國(guó)文化里產(chǎn)生的視覺(jué)現(xiàn)象,離開(kāi)了傳統(tǒng)的文化生態(tài),它的語(yǔ)言用來(lái)承載什么、表達(dá)什么,這是問(wèn)題的關(guān)鍵。我們當(dāng)下的教育體系,能夠讓我們對(duì)傳統(tǒng)文化有多少了解?我們的畫(huà)家傳統(tǒng)文化修養(yǎng)又有多深?我們的繪畫(huà)樣式,傳統(tǒng)的成分還有多少?
我們給藝術(shù)的發(fā)展畫(huà)了一個(gè)路徑,叫作“守正創(chuàng)新”,而其實(shí)呢,首先要搞清楚藝術(shù)最大的本質(zhì)是什么,藝術(shù)是時(shí)代的胎記、時(shí)代的投影,人的存在決定意識(shí),人存在的現(xiàn)實(shí)決定藝術(shù)形態(tài)。一部美術(shù)史就是一部社會(huì)發(fā)展史,藝術(shù)必須是與時(shí)代并行的,只有站立在當(dāng)下才具有價(jià)值,它的價(jià)值就是呈現(xiàn)當(dāng)下的生命經(jīng)驗(yàn),是對(duì)當(dāng)下的判斷、結(jié)論和思考。
所以,有什么樣的現(xiàn)實(shí)關(guān)照,就有什么樣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如果今天我們還在畫(huà)范寬、徐渭、八大山人,用他們的語(yǔ)言無(wú)法解釋當(dāng)下這個(gè)時(shí)代,藝術(shù)是創(chuàng)造性的,沒(méi)有創(chuàng)造不稱(chēng)其為藝術(shù)。
我們不必糾結(jié)中國(guó)畫(huà)應(yīng)該如何畫(huà),如果每個(gè)藝術(shù)家在當(dāng)下都能夠真實(shí)地表達(dá)自己,匯集起來(lái)就是這個(gè)世界最可靠的視覺(jué)記憶和判斷。因而藝術(shù)家真誠(chéng)地表達(dá)自己就夠了。當(dāng)然你需要去讀書(shū),去深入生活,然后才能使自己的表達(dá)變得更加深刻。
人的厚度決定了城市的高度
記者:所以,您認(rèn)為,中國(guó)畫(huà)的發(fā)展首先取決于藝術(shù)家個(gè)體的當(dāng)下創(chuàng)造。您個(gè)人是如何尋求當(dāng)下創(chuàng)造的突破的?在您看來(lái),水墨的創(chuàng)新語(yǔ)言究竟是形式上的創(chuàng)新,還是表現(xiàn)為內(nèi)容題材上的變化?
趙建成:傳統(tǒng)的中國(guó)藝術(shù)里面,在似與不似之間的寫(xiě)意精神最為可貴,“不似”是我們對(duì)自然的再理解,畫(huà)一座山,把我們的“意”放在里面,它就變成了一座精神的山,畫(huà)家以“意”的關(guān)照進(jìn)行再創(chuàng)造。當(dāng)我們面臨一個(gè)越來(lái)越復(fù)雜的世界,我們的手段是有限的。所以中國(guó)畫(huà)必然要在繼承之上尋求新突破,“徐蔣體系”提出“素描是一切造型藝術(shù)的基礎(chǔ)”的觀點(diǎn),就是中國(guó)畫(huà)尋求發(fā)展突破的一個(gè)必然。
來(lái)北京之后我一直在進(jìn)行歷史文化名人肖像畫(huà)的系列創(chuàng)作,我將之命名為《先賢錄》,已經(jīng)確定了100幅的創(chuàng)作目標(biāo),都是高2.6米的大尺幅。如今人們?cè)诶L畫(huà)的觀賞方式上也發(fā)生了變化,對(duì)一般畫(huà)幅是欣賞,而我希望大家去仰望、膜拜中國(guó)文化歷史中的一座座高山,能夠在創(chuàng)作中呈現(xiàn)他們深厚的傳統(tǒng)文化底蘊(yùn)以及學(xué)貫中西的正大氣象與廟堂風(fēng)范,用繪畫(huà)記錄對(duì)中國(guó)歷史進(jìn)程有重要作用與貢獻(xiàn)的賢者,他們是我們時(shí)代的精神坐標(biāo),沒(méi)有他們,我們的精神是漂泊的。
顯然,基于這樣一種理念來(lái)表達(dá)這些先賢,傳統(tǒng)的表達(dá)方式是不夠用的,這迫使我用全新的繪畫(huà)語(yǔ)言,去不斷嘗試實(shí)驗(yàn)性的畫(huà)法,這里面秉持傳統(tǒng)水墨的元素,又有當(dāng)代的筆墨結(jié)構(gòu)方式。
記者:那么今天,我們又將以什么樣的標(biāo)準(zhǔn)來(lái)評(píng)判當(dāng)代的水墨創(chuàng)作?
趙建成:我有四點(diǎn)評(píng)判標(biāo)準(zhǔn):一是繪畫(huà)語(yǔ)言的原創(chuàng)性,當(dāng)然要做到純粹的原創(chuàng)幾乎是不可能的,但要起碼超過(guò)六成;二是繪畫(huà)語(yǔ)言對(duì)時(shí)代的承載力,像我之前說(shuō)的,一定要與時(shí)代發(fā)生關(guān)系;三是繪畫(huà)語(yǔ)言的體系化,這是技術(shù)層面的難度,直接體現(xiàn)為作品的辯識(shí)度;四是語(yǔ)言對(duì)當(dāng)下和后世影響的廣度和深度。我認(rèn)為上述四點(diǎn),達(dá)到兩個(gè)方面,就是優(yōu)秀畫(huà)家,達(dá)到三個(gè)方面就是“大家”,四個(gè)方面都達(dá)到就稱(chēng)得上“大師”了。其實(shí)一個(gè)畫(huà)家說(shuō)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他的作品中體現(xiàn)了什么。
記者:再回到您的青島人身份,離開(kāi)青島之后,不知您對(duì)這座城市有怎樣的關(guān)注度?十多年過(guò)去了,您覺(jué)得它在藝術(shù)領(lǐng)域是否已經(jīng)發(fā)生了某種變化?
趙建成:在北京,唐國(guó)強(qiáng)曾經(jīng)到我的畫(huà)室來(lái),我們聊了很多。應(yīng)該說(shuō)青島在藝術(shù)界、演藝界出了很多好苗子,他們移植到各地深厚的土壤中,有了更大成就。青島人杰地靈,觀念新,不守舊,但是相對(duì)而言,一百多年的歷史文化積淀并不很深厚,我們必須承認(rèn)這一點(diǎn)。所以青島首先要正視的問(wèn)題是,如何在天然優(yōu)勢(shì)的基礎(chǔ)上,讓這片文化土壤變得肥沃,讓好苗子也能變得根深葉茂。青島首先應(yīng)該加大藝術(shù)人才引進(jìn)力度,認(rèn)識(shí)到人的重要性,畢竟,人的厚度決定了城市的高度。(青島日?qǐng)?bào)/觀海新聞?dòng)浾?李魏)
責(zé)任編輯:管佳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