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詩人、作家邵燕祥先生在睡夢中離世,享年87歲。“之前讀書,寫作,散步如常。清清白白,一切圓滿。”在得知這一消息后,學者、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陳子善寫道。
邵燕祥于1933年6月生于北京,祖籍浙江蕭山,曾任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編輯、記者,《詩刊》副主編,中國作協第三、四屆理事。著有詩集《到遠方去》《遲開的花》《邵燕祥抒情長詩集》等,上世紀80年代后又發表大量雜文、散文,晚年作有《一個戴灰帽子的人》《我死過,我幸存,我作證》等回憶錄作品。曾獲首屆魯迅文學獎。
邵燕祥早年以新詩聞名,尤其長于歌頌新生活和新景象的贊美詩。在出版于2003年的《邵燕祥自述》中,邵燕祥寫道,這是他當時主動放棄散文、小說創作的結果。但在1958年初,邵燕祥被錯劃為右派,直到1979年1月才獲得改正。“重獲新生”后,他已經從一個極為熱烈天真的追隨者,轉變為一個清醒尖銳的探求者,不斷用雜文進行發問、批判與反思。

在一次個人詩歌研討會上,邵燕祥說道:“詩的核心價值是自由。離開心智的自由,離開對自由的追求,就沒有真正的詩。” 局限于直接的政治意義,詩歌便會淪為口號。
對于雜文寫作,邵燕祥則說:“雜文的靈魂是真理的力量,邏輯的力量。” 他的雜文具有鮮明的啟蒙理性色彩。由于邵燕祥的寫作針砭時弊、直面生活,評論界曾有人稱他為“當代魯迅”。邵燕祥得知后連忙推辭,“魯迅,無論過去、現在或將來,都只有一個”,但他也承認,自己把魯迅引為師友,視為知己,高山仰止。
“即使魯迅平生只寫過一句話,就是《祝〈濤聲〉》中的‘名列于該殺之林則可,懸梁服毒,是不來的’,我就會終生視他為知己。”1947年秋,中共地下黨組織遭到破壞時,邵燕祥正好讀到魯迅的這句話,從此便把它當作座右銘牢記。在被劃為右派、下放勞改最壓抑的時期,他也給自己定下了“決不自殺”的底線,正是這句話給予的力量。
邵燕祥的雜文除了去揭露、去批判,更不乏對自己的反省,這點也與魯迅相似。他在一篇雜文集的附記中寫道,如果不能學習魯迅那種在解剖社會人事的同時也時時解剖自己,而只一味當“手電筒”——光照亮別人,不照自己,只知指手畫腳地進行說教,恐怕雜文將失去讀者,做人也將失去朋友的。
在反右運動50周年時,邵燕祥曾自問,“我是不幸中的幸者,比起已死的人,我活了下來,比起破家的人,我尚有枝可依。”
最后得到的答案是,作為幸存的不幸者,他要書寫、要記錄、要為歷史作證。于是便有了之后的《一個戴灰帽子的人》和《我死過,我幸存,我作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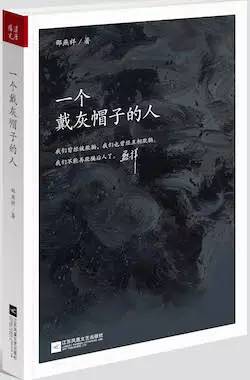
《一個戴灰帽子的人》,作者: 邵燕祥,版本: 江蘇文藝出版社 2014年7月
在出版于2014年的《一個戴灰帽子的人》中,邵燕祥以真誠、樸實的筆觸回憶了自己1960年至1965年六年的“右派”時光,并大聲疾呼,“我們曾經被欺騙,我們也曾經互相欺騙。我們不能再欺騙后人了。”
而在2016年出版的《我死過,我幸存,我作證》,他以親身經歷為基礎,記述了1945年至1958年中國社會的歷史變遷。此時他已83歲高齡,仍筆耕不輟,勤奮地、急切地寫作著。
今年年初,邵燕祥先生曾接受《中華讀書報》的采訪,聊自己的枕邊書。《魯迅全集》是他最初閱讀,也是最常閱讀的書籍。他至今記得,初中第一冊的國文課本,第一篇是巴金的《繁星》,第二篇就是魯迅的《秋夜》。當時他的哥哥還買過魯迅的《彷徨》和田漢改編的《阿Q正傳》劇本,他常借來翻看。
當時最流行的書籍武俠小說《蜀山劍俠傳》、《青城十九俠》,邵燕祥也看得如饑似渴。不過,“武俠小說當然比魯迅巴金的作品更吸引人,但我們的確只拿它解悶。”
張恨水的《啼笑因緣》,邵燕祥年幼時就看得出神,長大后再看更覺得滄桑感遠超一般的鴛鴦蝴蝶派。而且不僅他的母親愛看,他的岳母也愛看,魯迅也曾買來寄給自己的母親,“不說全世界吧,全中國的老太太都愛看《啼笑因緣》。”
到了86歲,邵燕祥仍然幾乎每年都要重看一遍《魯迅全集》,尤其是其中1到6卷雜文的部分,常讀常新。他也仍然保持著作文、作詩的習慣,只是不再出于創作激情,而是源于生命的滄桑。
他上世紀80年代出版的詩作《云南驛懷古》,也許正好可以借來紀念他的一生:
我是歷史,奔跑在古驛道上,
多少星霜。天天踐著晨霜上路,
直跑到西山山影落在東山上。
清冷的星斗篩進馬槽,
秦時明月漢時關,歷盡興亡。
奔跑過多少烽臺堠望,
驛站荒涼。荊棘蔓草
長滿了當日的迷宮阿房。
我叩問人民;秦贏政
怕不如一曲民歌壽命長。
驛道上,也曾有鮮荔枝飛馳而往,
紅塵飛揚。百姓長年陷身于水火,
而華清池四季溫湯。
李隆基,我不忍呼你為淫棍,
你早年曾是個有為的君王。
永遠是如此行色倉皇,
漏夜奔忙。說什么關山難越悲失路,
負重致遠的才是民族的脊梁。
從來草野高于廟堂,
莽蒼蒼,一萬里關山風起云揚。
責任編輯:單蓓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