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蕓齋小說(shuō)》可以說(shuō)是孫犁以往生活的影子。孫犁晚年寫《蕓齋小說(shuō)》所憑借的幾乎都是他生活里的記憶和熟悉的人物——當(dāng)然是以人物為小說(shuō)的原型。其中有幾篇引起我的興趣,就是想查證一下小說(shuō)的人物原型又是誰(shuí)呢?例如寫王曼恬,再如那篇《羅漢松》里面的主人公 “冀中的莫里哀”。其實(shí)稍微了解一下抗戰(zhàn)時(shí)期冀中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也很容易看出:小說(shuō)《羅漢松》的主人公老張就是以冀中抗戰(zhàn)作家王林為原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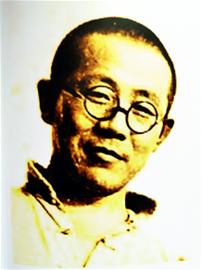
1946年王林像。
曾就讀于國(guó)立青島大學(xué)
孫犁在筆記小說(shuō)《羅漢松》里,塑造了一個(gè)游戲人生的作家形象。在這篇小說(shuō)的最后,孫犁寫道:“歷次政治運(yùn)動(dòng),他都以老運(yùn)動(dòng)員,或稱為老油條的功夫,順利通過(guò)。 ”“據(jù)我思考,老張得力之處,在于處事待人。他不像一般作家那樣清高孤僻,落落寡合。什么人他都交接,什么事都談得。特別是那些有權(quán)有勢(shì),對(duì)他有用的人。他以作家的敏感,去了解對(duì)方的心意;然后以官場(chǎng)的法術(shù),去討得他們的歡心。”“噫!當(dāng)年革命如渡急湍,政治如處漩渦。老張不只游戲人生,且亦游戲政治。其真善泳者乎! ”
最初我以為王林(1909—1984)只是一位“三八式”的老干部,與孫犁一樣,是抗日軍興參加八路軍獻(xiàn)身抗戰(zhàn)的青年知識(shí)分子。后來(lái)才得知,王林1909年生于河北省衡水縣,曾就讀于國(guó)立青島大學(xué)(即國(guó)立山東大學(xué)的前身)。在青島讀大學(xué)時(shí),他還是中共青島大學(xué)地下黨的支部書記,與黃敬等人一個(gè)支部。他在青島大學(xué)讀書期間,是沈從文小說(shuō)訓(xùn)練班的學(xué)生,還在沈從文主編的天津《大公報(bào)》文藝副刊和《國(guó)聞周版》文藝欄發(fā)表了一系列鄉(xiāng)土題材的文學(xué)作品,并出版了長(zhǎng)篇小說(shuō)《幽僻的陳莊》。沈從文評(píng)價(jià)王林說(shuō):中國(guó)倘如需要所謂用農(nóng)村為背景的國(guó)民文學(xué),我以為可注意的就是這種少壯有為的作家。這個(gè)人不獨(dú)對(duì)于農(nóng)村的語(yǔ)言生活知識(shí)十分淵博,且錢莊、軍營(yíng)以及牢獄、逃亡,皆無(wú)不在他生命中占去一部分日子。他那勇于在社會(huì)生活方面尋找教訓(xùn)的精神,尤為稀有少見(jiàn)的精神 。
王林最重要的作品就是長(zhǎng)篇小說(shuō) 《腹地》。 《腹地》以1942年日軍對(duì)冀中平原“五一”大掃蕩為背景,記錄了作者所親歷的冀中反掃蕩生活。在冀中反“掃蕩”時(shí),冀中軍區(qū)機(jī)關(guān)人員撤離轉(zhuǎn)移到太行山區(qū)。王林時(shí)任冀中軍區(qū)火線劇社社長(zhǎng),屬于這次轉(zhuǎn)移之列,但他要求留下堅(jiān)持斗爭(zhēng),他是這樣說(shuō)的:“作為一個(gè)文藝寫作者,我有責(zé)任描寫這一段斗爭(zhēng)歷史,我不能等時(shí)過(guò)境遷,再回來(lái)根據(jù)訪問(wèn)和推想來(lái)寫。我要做歷史的一個(gè)見(jiàn)證人和戰(zhàn)斗員,來(lái)表現(xiàn)這段驚心動(dòng)魄的民族戰(zhàn)爭(zhēng)史。 ”王林表示:“冀中最后留下一個(gè)干部,那就是王林!最后剩下一個(gè)老百姓,那也是王林!”王林說(shuō):“這正如同演戲演到高潮一樣,我不能中途退場(chǎng)。我要作為歷史的一個(gè)見(jiàn)證人和戰(zhàn)斗員,來(lái)表現(xiàn)這段驚心動(dòng)魄的民族革命戰(zhàn)爭(zhēng)史。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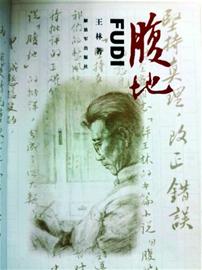
1985年版《腹地》封面。
四處隱藏轉(zhuǎn)移中完成寫作
王林1942年冬開(kāi)始動(dòng)筆,1943年夏完成《腹地》初稿。他是在四處隱蔽和轉(zhuǎn)移的過(guò)程中寫下了冀中平原反抗日軍掃蕩的《腹地》一書,他后來(lái)回憶說(shuō):“因?yàn)閿橙说狞c(diǎn)碉如林,汽車路、封鎖溝密如蜘蛛網(wǎng),隨時(shí)隨地都可能與敵人相遇。我雖堅(jiān)信最后勝利一定屬于中華民族,但并不敢幻想自己能夠在戰(zhàn)火中幸存。我就這樣,像準(zhǔn)備遺囑一樣,蹲在堡壘戶的地道口上,開(kāi)始了《腹地》的寫作……寫完一疊稿紙,就封閉在地道里。 ”
小說(shuō)《腹地》的主人公叫辛大剛,是一位因傷致殘回到村中的八路軍戰(zhàn)士。他參加了劇團(tuán),并跟劇團(tuán)里的一位美麗的姑娘白玉萼相愛(ài)。村支書范世榮是破落地主后代,喪妻后想將白玉萼續(xù)弦,于是在村中開(kāi)會(huì)批判辛大剛。此時(shí),日軍開(kāi)始了殘酷的“五一”大掃蕩,村支書卻躲到了親戚家。危急之時(shí),辛大剛帶領(lǐng)村民開(kāi)始了反“掃蕩”斗爭(zhēng)……
在《腹地》完成后,孫犁曾如此評(píng)價(jià)《腹地》:“這是一幅偉大的民族苦難圖,民族苦戰(zhàn)圖,作者王林自始至終親身經(jīng)歷了這個(gè)事變 。寫反掃蕩是本書最拿手最成功的地方。當(dāng)然,本書最精彩的地方還是真正寫出了地道的冀中人民的生活的戰(zhàn)斗的情緒。因?yàn)樽髡邔懙牟恢皇且环N無(wú)可奈何的苦難,也不是單純以故事傳奇動(dòng)人的英雄故事。這是一幅嚴(yán)峻的甚至殘酷的現(xiàn)實(shí)圖畫……沒(méi)有傳奇,沒(méi)有編造,沒(méi)有粉飾。 ”
1946年,王林將《腹地》手稿本拿給文藝界朋友們看,征求意見(jiàn)。曾在延安魯藝任戲劇系主任的張庚提意見(jiàn)說(shuō):“第一節(jié)到第六節(jié)氣魄大,但辛大剛到劇團(tuán)中搞戀愛(ài)去了……這村前后兩任支書皆壞蛋,令人不知光明何在。 ”1949年5月,作家康濯寫信給王林:“花了兩天時(shí)間,看完了大作《腹地》,我激動(dòng)得不行!我拼命找黑暗,但找不著!我拼命找‘看不出人民力量’的東西,但人民力量都向我涌來(lái)!難怪王林要發(fā)瘋了? ”丁玲建議王林“將《腹地》給周揚(yáng)寄去”,周揚(yáng)看過(guò)部分章節(jié)后,認(rèn)為修改一些部分即可出版。周揚(yáng)說(shuō):“別人說(shuō)這本小說(shuō)把解放區(qū)寫得太黑暗,我看寫得還太光明了呢,冀中區(qū)那個(gè)時(shí)候的工作就那樣深入嗎? ”在周揚(yáng)的支持下,1949年8月20日,《腹地》在天津開(kāi)始排印。當(dāng)時(shí),王林已隨部隊(duì)進(jìn)入天津,任天津總工會(huì)文教部部長(zhǎng)。之后又任天津文聯(lián)黨組副書記等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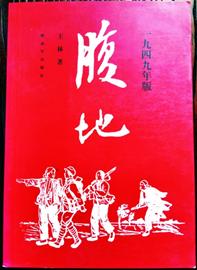
2007年王林《腹地》1949版重版。
日記見(jiàn)證與孫犁友情
1950年5月,《腹地》在上海再版。在1950年第27期、第28期《文藝報(bào)》上,該報(bào)副主編陳企霞發(fā)表了長(zhǎng)達(dá)兩萬(wàn)多字的《評(píng)王林的長(zhǎng)篇小說(shuō)〈腹地〉》。這篇批判文章發(fā)表后,新華書店很快就全部下架此書。這也是王林命運(yùn)的拐點(diǎn)。
由于《腹地》不能再版,王林便不斷進(jìn)行修改。 《腹地》被王林視若生平最重要的作品,爭(zhēng)取改好重新出版,便成為他后半生的主要精神訴求。在他去世前終于完成,并在他去世后的1985年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再后來(lái),王林的兒子王瑞陽(yáng)“發(fā)現(xiàn)”了自己父親最初版本的《腹地》。在《老照片》第70輯上,有一篇王瑞陽(yáng)寫的《父親王林與“腹地”》,介紹了這部長(zhǎng)篇小說(shuō)與作家的命運(yùn)。2007年,王瑞陽(yáng)自費(fèi)由解放軍出版社重新出版了1949年版《腹地》。
孫犁在《羅漢松》里對(duì)老張的描寫,很難對(duì)王林不產(chǎn)生聯(lián)想。王林和孫犁是多年的戰(zhàn)友,也是作家同行。但兩人的性格和處事明顯不同,若讀王林的日記,可以看出兩人之間的友情和上世紀(jì)50年代初期兩人因文學(xué)作品遭遇的處境——
1950年 1月21日
晚到孫犁處,他的老婆躺在炕上,他坐在床上,孩子們圍著玩,孫對(duì)自己的創(chuàng)作也感到苦惱。不外幾個(gè)女孩子,不過(guò)換過(guò)名字算啦。他想打出這圈子去,我感覺(jué)他這話倒是很深刻的自我批評(píng),同時(shí)也是向前躍進(jìn)的開(kāi)始。
1951年11月6日
在青島時(shí)接到孫犁同志出國(guó)前信,說(shuō)《光明日?qǐng)?bào)》對(duì)他有兩文批評(píng)。回到津向鄒明同志取剪報(bào)來(lái)看,批評(píng)者似乎對(duì)孫犁同志很了解,林、張文中說(shuō)他在農(nóng)村中生活過(guò)一段時(shí)期。在青島時(shí)以為是批評(píng)《風(fēng)云初記》,原來(lái)只是舊作《鐘》和《囑咐》……
1952年12月29日
今晨醒來(lái),想起昨天看到的留里可夫的論文和孫犁同志的聊天,又想到幾年來(lái)內(nèi)心的痛苦,不知為何涌出眼淚,幾年來(lái)教條主義者打擊得我已經(jīng)喪失了正視生活的勇氣,弄得頭昏眼花,鬧不請(qǐng)現(xiàn)實(shí)主義是怎么回事了,以為勝利者只需要粉飾太平。
1956年1月29日
前晚王亢之部長(zhǎng)批評(píng)我和孫犁同志主要問(wèn)題是社會(huì)主義積極性不夠。
1956年4月4日
晚至孫犁同志處看他,他上星期四因勞累,午睡后小便后暈倒,把左腮跌破,尚未檢查出究竟是何病。身體是作家趕生活浪潮的本錢,這事對(duì)老孫的挫傷不小。
1957年1月2日
孫犁同志1956年的新作今日讀完,很有詩(shī)意。我今看來(lái),也覺(jué)得是孫犁的杰作。
1957年8月2日
二日到小湯山看孫犁同志,他的病見(jiàn)好,穩(wěn)定住了,就是好。
1958年6月21日
評(píng)介孫犁同志的《白洋淀紀(jì)事》的文章,昨天寫出了主段,今早安了個(gè)尾巴,這也算還了多日壓在心上的一個(gè)問(wèn)題,也算對(duì)老友的一個(gè)懷念。
1960年6月24日
上午梁斌同志來(lái)談,遠(yuǎn)千里同志在去年全國(guó)文化會(huì)議小組會(huì)上提出對(duì) 《鐵木前傳》和《十八匹戰(zhàn)馬》的批評(píng)。下午林吶同志來(lái)說(shuō)人民圖書館評(píng)論組正討論《鐵木前傳》,持否定論點(diǎn)者居多數(shù)。語(yǔ)文研究所張果總結(jié)大家的意見(jiàn)而又加以提高說(shuō):自然主義手法、修正主義思想……
《十八匹戰(zhàn)馬》是王林的短篇小說(shuō)。孫犁1956年“很有詩(shī)意的杰作”就是中篇小說(shuō)《鐵木前傳》。也就是說(shuō),王林和孫犁都因?yàn)樽约旱男伦饔衷獾脚u(píng)。
晚年的孫犁曾寫過(guò)多篇懷念冀中抗戰(zhàn)時(shí)期作家戰(zhàn)友的紀(jì)念文章,例如懷念作家遠(yuǎn)千里、詩(shī)人田間等。但是,除了這篇筆記小說(shuō)《羅漢松》,再?zèng)]見(jiàn)過(guò)他寫王林的紀(jì)念文章。(文/薛原 本版圖片均由作者整理提供)
責(zé)任編輯:李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