膠東經濟圈近期成為了一個熱詞。
從古至今,膠東地區(qū)民俗相近、人文相通,歷史文化也一脈相承。對于秦代以后膠東的歷史,很多人比較了解,很多史料對這段歷史也梳理得十分清楚。而對于遠古到秦代的歷史脈絡,大部分史料鮮有涉及,或只有零星記載。筆者用時一年,選讀了《尚書》《左傳》《史記》《資治通鑒》等相關章節(jié),通讀了錢穆先生的《秦漢史》、呂思勉先生的《先秦史》《秦漢史》、白壽彝先生主編的《中國通史綱要》,力圖把遠古至秦代的膠東歷史做一清晰明了的梳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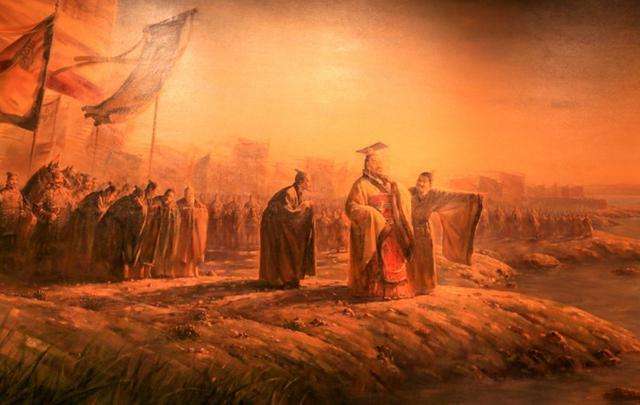 一
一
東夷,遠古三大部落之一
膠東,在遠古時代就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區(qū)域。《尚書·禹貢》中有“萊夷”、“嵎夷”之說,萊夷是以萊為名的夷人;嵎夷則指膠東濱海地區(qū),嵎的本意是山勢彎曲險阻。
據白壽彝先生《中國通史綱要》考證,東夷部落與西方的炎黃部落、南方的苗蠻部落是同時并存的三大部落集團。
中華民族一般尊稱炎帝和黃帝為祖先。炎帝部落是姜姓,黃帝部落是姬姓,均生活于黃河中上游渭河流域。他們屬于近親部落,后來結成了聯(lián)盟,并沿黃河兩岸向東發(fā)展,活躍在今山西、河南、河北一帶。舜和禹傳說是黃帝的后代,是他們的部落首領。
在南方的長江流域,則有大量苗蠻部落存在,他們主要活躍在湖北、湖南、江西一帶。伏羲和女媧是他們的首領。伏羲教會民眾用繩索織網,打獵捕魚;女媧煉五色石補天,平定水土,除掉兇猛的鳥獸,二人都是苗蠻部落的遠祖。
東方的一些部落被稱為夷。白壽彝先生在《中國通史綱要》(下稱《綱要》)中說,夷部落的分布主要以山東東南部為中心,向北到河北南部,向西到河南東部,向南到安徽中部,向東直到大海。夷人以制造弓矢聞名,“夷”字本身就是一個背著弓的人。太昊,少昊和蚩尤是他們的部落首領。歷史上關于太昊、少昊的傳說很多,關于黃帝與蚩尤在涿鹿之野發(fā)生過大戰(zhàn)的記載也不乏其述。《綱要》認為,神話傳說中射日的后羿,就是東夷人有窮氏的后代,后來后羿還起兵攻打夏朝,做了王。關于羿代夏政的事,《左傳》中有詳細記載。關于神農、黃帝、蚩尤等的活動軌跡,呂思勉先生在《先秦史》中有詳細的考證。
公元前21世紀至公元前18世紀,是中國第一個王朝夏的統(tǒng)治時期。夏王朝由禹建立,其活動范圍基本延續(xù)了炎黃部落的活動區(qū)域。夏王朝建立初期,其部落聯(lián)盟首領是由夏和夷輪流擔任的,但后來禹的兒子啟破壞了這種推選制度,變成了“家天下”的世襲制。
夏朝歷經四百多年,共十四世十七王。到了少康的兒子杼的時候,發(fā)明了盔甲。有了盔甲的夏開始了對善于射箭的東夷的征戰(zhàn)。他們一路向東,迫使善射的東夷部落歸附了夏。自此,東夷做為一個獨立部落不復存在。
東夷與夏的融合,或者說,膠東文明與黃河流域文明的融合,可以看作中華民族融合版圖上的第一次文明交匯。
公元前18世紀末至公元前11世紀為商朝,歷經六七百年,共十七代三十一王。在這一漫長的歷史時期,關于東夷的記載少之又少。據《左傳》《中國歷史綱要》記載,商朝的末代王紂王曾親自率兵征伐東夷,苦戰(zhàn)一年,取得了對東夷作戰(zhàn)的勝利。而從商紂帶兵征伐東夷這一史實可以推測,遠古的東夷雖然歸附了夏和商,但與夏、商往往處于分分合合的狀態(tài)。
 二
二
萊(子)國與齊人滅萊
史學界普遍認為,古萊國(亦稱萊子國)是商代所封候國,到了西周時期發(fā)展為諸侯大國,后歷經商和西周,于東周時齊靈公15年(公元前567年)被齊所滅。古萊國最初的統(tǒng)治范圍西起臨朐、壽光的彌河,北至渤海,南至諸城、膠州一代,東到膠東半島。后在齊國的擠壓下,主要活動范圍縮小至膠東中北部。它的國都在黃縣(龍口)南六公里的古城遺址歸城,當地人又稱灰城,現在文登、萊陽一帶的方言還稱西部來的人為西萊子。
萊子國出土的鐵器和青銅器說明其冶煉技術已達到很高的水平。史料記載,齊國滅掉萊子國,齊靈王為表彰功臣叔夷,“賞城一座,縣二百,造鐵四千人”。這四千個鐵匠便是俘獲和受降的萊子國冶煉工,其冶鐵技術和規(guī)模可見一斑。現當地仍有冶基姜家等古村落名。據范文瀾先生考證,冶鐵技術很可能是東夷人首先發(fā)明。當地水草豐滿,盛產海鹽、葛布、蠶絲,而這些物品皆為西周東部爭相購買和上貢的佳品。
司馬遷在《史記·夏本紀》中記載,周武王平定天下,建立周朝后,封尚父(姜尚)于齊,最初定都營丘(有昌樂、臨淄、壽光三種說法)。就職路上,“逆旅之人”告訴他,“萊正日夜兼程,趕至營丘”。于是姜尚率兵急進,到達營丘作戰(zhàn),結果萊夷人戰(zhàn)敗,退回了膠東半島。后來,齊魯兩國聯(lián)合才滅掉了萊子國,齊國才真正強大起來。
 三
三
春秋戰(zhàn)國時期齊國的強盛與膠東的繁榮
從春秋時期的諸侯林立,到戰(zhàn)國時期的七雄割據,齊國憑借強人政治、賢相治國以及優(yōu)越的地理位置和豐富的物產,一直是七雄之中的佼佼者。
齊桓公倡導“尊周”,率領齊、魯、宋、鄭、陳、衛(wèi)、許、曹等“八國聯(lián)軍”討伐楚國,迫使楚王向周王進貢;任用管仲為相,推行富國強兵之政;九次大會諸侯。又如,公元前354年,魏國攻打趙國,齊將孫臏圍魏救趙;公元前342年,魏攻韓,孫臏帶兵誘敵輕進,俘虜魏太子申,逼迫主將龐涓自殺。齊國的強大,從秦國名士蘇秦在齊威王面前的陳述中可見一斑:“臨淄之中七萬戶,不下戶三男子,而臨淄之卒固二十一萬也。國都之中,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揮汗成雨”。
是時,膠東地區(qū)已非常富庶。司馬光《資治通鑒·周記》中記載,公元前370年,齊威王召見即墨大夫:“與之曰,吾使人視即墨,田野辟,人民給,官無事,東方以寧”,并封之萬家。田地原野被廣泛地開發(fā)、種植,人民富足,政治清明,整個齊國東部一片安寧祥和,足可見當時膠東地區(qū)的經濟發(fā)展和社會治理水平。
四
樂毅攻齊與田單復國
齊燕戰(zhàn)爭齊國的失敗,一是犯了戰(zhàn)略性錯誤,在秦國與其他五國作戰(zhàn)時,作壁上觀,沒有識破秦“連橫”戰(zhàn)略的危害;二是犯了戰(zhàn)術性錯誤,對燕國進行長達35年的征伐,大大消耗了實力,當秦軍兵臨城下時已無暇自顧。
公元前314年,齊國趁燕國內亂,舉兵攻入燕國都城,“燕士卒不戰(zhàn),城門不閉”,齊國將士趁機殺死了燕王噲。
公元前284年,燕昭王以樂毅為大將軍,約趙、衛(wèi)之兵一并討伐齊國。齊泯王廢黜賢良,驕奢暴戾,百姓怨懟。由于齊泯王失去民心,趙燕之兵所向披靡,六個月之內拔下了齊國七十余城。《資治通鑒·周記四》記載,“燕師乘勝長驅,齊城皆望風奔潰”。
樂毅所到之處,禁止侵掠;找到逃跑的百姓,對他們以禮相待;少賦斂,除暴令。他還在郊野祭祀齊國立國之君齊桓公和立國之相管仲,極大拉攏了民心,“齊民喜悅”。
樂毅又派左軍攻打膠東、東萊;派前軍循泰山以東至海,占領瑯琊;派中軍占領臨淄。齊泯王跑到衛(wèi)國,又從衛(wèi)國逃到了鄒國和魯國,都不受歡迎,最后只好逃回自己的屬地莒。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樂毅攻齊與齊王走莒。
樂毅伐齊,卻在只剩下莒和即墨兩城時,圍而不打,一年之后“令士兵各去城九里而圍壘”,還下令曰:“城中民出者,勿獲;困者,賑之;使即舊業(yè)”。而且,這一政令一堅持就是三年。
后來,昭王去世,惠王繼位。燕惠王本就與樂毅有隙,加之讒言和齊國的反間計,惠王硬是把樂毅從前線召回。樂毅怕招來殺身之禍,去了趙國。
樂毅被撤換,換來了即墨城的復興。這就有了后來被民眾津津樂道的火牛陣、田單復國和田單相齊。“田單乃收城中得千余牛,為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噪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
后來,田單帶著日益增多的兵馬將燕軍一路追殺過了黃河,把燕軍占領的70余座城池全部收復,又到莒地迎接襄王。復國后,田單被封為安平君,隨后做了齊國的宰相。為褒獎其功績,齊王把夜夷(即今萊州一帶)萬戶人家封給了田單。
五
秦王滅齊與始皇三次東巡
齊國的滅亡,主要原因是齊王受了秦國的利誘和欺騙。《資治通鑒·秦記始皇帝記下》記載,始皇26年(公元前221年),“秦使人誘齊王,約封以500里之地。齊王遂降”,后被餓死。白壽彝先生在《綱要》中說,齊國的貴族接受秦國的黃金最多,齊國是在完全不抵抗狀態(tài)下投降的。
齊國的滅亡正式標志著戰(zhàn)國時期的結束和秦朝的開始。
秦統(tǒng)一時全國設三十六郡。現山東地區(qū)為瑯琊郡(約泰山小清河以東,原沂河入海口以北,包括膠東半島的廣大地區(qū))、齊郡(約泰山以北,小清河以西地區(qū))和薛郡(約濟寧棗莊一帶和蘇北地區(qū))。也就是說,現在的“膠東經濟圈”那時完全屬于瑯琊郡。后秦朝又將三十六郡改為四十八郡。就現山東地區(qū)而言,從瑯琊郡分出膠東郡;將齊郡分為臨淄郡和濟北郡;薛郡保留,但疆域變小;又在江蘇和皖北地區(qū)新設了東海郡。至此,膠東正式變?yōu)榍爻囊粋€省級行政區(qū)劃——“膠東郡”。
始皇三次東巡,呂思勉先生在《秦漢史》(第二版)中做了詳細考證。第一次東巡時間在始皇28年(公元前219年)。從咸陽出,到鄒嶧山(今山東鄒縣),至泰山,從南面登至山巔,立石頌德,從北面下山。沿渤海岸一路向東,“過黃(今龍口)、腄(今福山區(qū))”,登上了芝罘山,到達榮成成山頭,立石頌德,然后一路向南登瑯琊。《資治通鑒》這樣記載:“南登瑯琊,大樂之。留三月,作瑯琊臺,立石頌德,明得意。”
本來是宣揚文治武功的走馬觀花,秦始皇竟然在這里住了三個月,可見膠東和瑯琊風景之引人入勝,也可以想象始皇帝“大樂之”的情景。
據呂思勉先生考證,在此次東巡過程中,秦始皇從外地遷來了三萬戶百姓,安排在瑯琊臺腳下,前前后后歷時12年。三萬戶,按照蘇秦“一戶三丁”的說法,至少是一家四口,即至少12萬人來到了現在的瑯琊。這應該是青島甚至膠東歷史上第一次人口大遷入。
第二次東巡發(fā)生在始皇29年(公元前218年),也就是第一次東巡的第二年。這一次先到了河南,從河南“登芝罘,刻石,旋之瑯琊”。怎么從河南去的煙臺芝罘,途徑哪里,史書沒有記載。為什么不是走近路先到瑯琊再去芝罘也不得而知。但有意思的是,司馬遷用了一個“旋”字,就是皇帝到了芝罘后立刻就離開,馬上就到了瑯琊。我們可以想象,可能因為秦始皇忘不了瑯琊美景,以及去年三個月居住于此的美好時光。
第三次東巡是在始皇37年(公元前210年),與第一次相距八年。這一次出游,丞相李斯與始皇的小兒子胡亥隨從。前一年十月出發(fā),十一月先到了湖南,又沿長江而下,到了今安徽潛山、當涂一帶。后又到了浙江杭州、會稽一帶,在那里祭祀了大禹,并刻石紀念。后渡過長江,從江蘇句容縣沿著海岸線到達了瑯琊,又從瑯琊沿海邊到了榮成成山,從榮成成山到了煙臺芝罘。之后沿著海邊一路西行到達今山東平原縣,發(fā)病。七月份到達巨鹿沙兵(今河北平鄉(xiāng)縣),駕崩。
據呂思勉先生考證,秦始皇在瑯琊時做了一個奇怪的夢,夢見與相貌如人一樣的海神作戰(zhàn)。經占夢博士解夢,此非祥兆。于是命令手下人到海中去捕巨魚,打算捕住之后親手射殺。可自瑯琊北至榮成山都沒有逮到大魚。到了芝罘,終于見了巨魚,“始皇帝射殺一魚”。
據《資治通鑒·秦紀》記載,秦始皇在統(tǒng)一六國后,總計有五次大的出巡。除上述三次外,第一次是始皇27年,向西巡隴西、北地;還有一次是始皇32年,向北到達碣石、上郡。執(zhí)政三十七年,五次巡視,三次到達今天的膠東經濟圈,三登芝罘,三登瑯琊,兩臨榮成,由此可見瑯琊郡和膠東郡在秦朝的重要性,也可以看出膠東地區(qū)在始皇帝心中的份量。
從遠古時期做為與炎黃、苗蠻并列的三大部落,到冶鐵、制鹽、葛絲業(yè)發(fā)達的古萊國,從做為戰(zhàn)國時期成就霸業(yè)的齊國東部相對繁榮和富足的五都之一,到秦統(tǒng)一全國后戰(zhàn)略、經濟和文化價值都特別重要的瑯玡郡、膠東郡,當我們回溯這段歷史的時候,就會發(fā)現,今天的膠東地區(qū),歷史是悠久的,文明是源遠流長的。所謂的“蠻夷之地”,實際上是站在黃河流域文明的視角;當我們站在更寬大的視野研究時,就會發(fā)現,膠東和黃河流域一樣,也是中華民族古老文明的發(fā)祥地之一,并且,東夷部落代表的東夷文化最早與炎黃部落代表的黃河文明融為一體,成為中華文明的一部分。同時,我們還會發(fā)現,整個膠東地區(qū)經濟的相對發(fā)展和富庶,并非近代開埠以來的事,而是從遠古、萊國、齊國、秦代既已有之。這與膠東地區(qū)優(yōu)越的地理位置、適宜的氣候條件、豐富的自然稟賦,以及先民的探索和創(chuàng)新,是密不可分的。
研究歷史是為了更好地認識現在和發(fā)展未來。廓清了這段歷史,就可以讓我們更加增強建設膠東經濟圈的歷史自信和文化自信,以更大的歷史自覺擔當起繼往開來的時代使命。
(來源:山東科技大學官微 作者簡介:武善領,文化學者,出版過《審美教育》(山東友誼出版社)等專著;在《文學評論》、《山東文學》等國家、省級刊物發(fā)表評論、詩歌等20余篇。1991年加入山東省作家協(xié)會。西海岸新區(qū)教育和體育局工作。)
責任編輯:楊海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