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25日,中國人民志愿軍打響了入朝作戰的第一槍。六年后,第一部反映抗美援朝的電影《上甘嶺》上映,插曲《我的祖國》傳唱至今。
上世紀六十年代拍攝的《英雄兒女》再次奉獻了“為了勝利,向我開炮”和《英雄贊歌》等經典元素。
然而此后幾十年間,再也沒有出現能媲美以上兩部的抗美援朝電影,在電影市場商業化的2000年后,更是只有馮小剛的《集結號》出現過相關情節。
七十年前,一百三十萬志愿軍渡過鴨綠江,其中近二十萬人再也沒能回來,他們灑下熱血凝結成延續至今的和平,我們需要光影來記住那日漸遠逝的榮光。

殘酷戰場
1952年10月,位于朝鮮中部五圣山南麓的上甘嶺爆發激戰。在第一天的戰斗中,志愿軍一三五團九連和一連就把儲備的彈藥打光了,共發射了四十萬發子彈,手榴彈、手雷近萬枚,打壞機槍幾十挺,占全部武器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上甘嶺的血戰持續了43天,殘酷程度世所罕見,也是影響戰爭全局的關鍵一戰。
戰役結束兩年后,導演沙蒙帶隊到上甘嶺實地考察,他們先是陶醉在漫山遍野的金達萊花里,但走過那個山頭一看,就像天堂與地獄的分界線,眼前的景象變得黑糊糊的,沒有一棵活著的樹,在戰斗英雄黃繼光犧牲的597.9高地主峰上,整個山頭都被劈開了,山上被填塞的坑道里還有烈士的尸骨。
經過兩個月的朝鮮之行,四個月的國內采訪,電影《上甘嶺》進入劇本創作階段,21歲的演員張亮扮演通訊員楊德才,這個角色的原型就是黃繼光。
拍飛身堵槍眼那天,導演在收工后把他叫住,說要加一個鏡頭,即楊德才在撲到敵人機槍口的瞬間,回頭喊了一聲,“連長!”
在真實的戰斗中,黃繼光喊了什么沒有人知道,當時他受傷趴在地上,往前面扔了一顆手榴彈,戰友們等手榴彈炸響就準備沖鋒,但剛站起來,就被敵人的機槍壓了下去。
這時,黃繼光抬起頭往后面望了望,爬到敵人的工事旁邊,然后朝戰友的方向喊了幾句話,但機槍聲太大,誰都沒聽見,最后他就用手抓著麻袋,狠狠地使勁上去,堵住了槍眼。
電影中楊德才犧牲時喊的那一聲“連長”,讓許多觀眾記憶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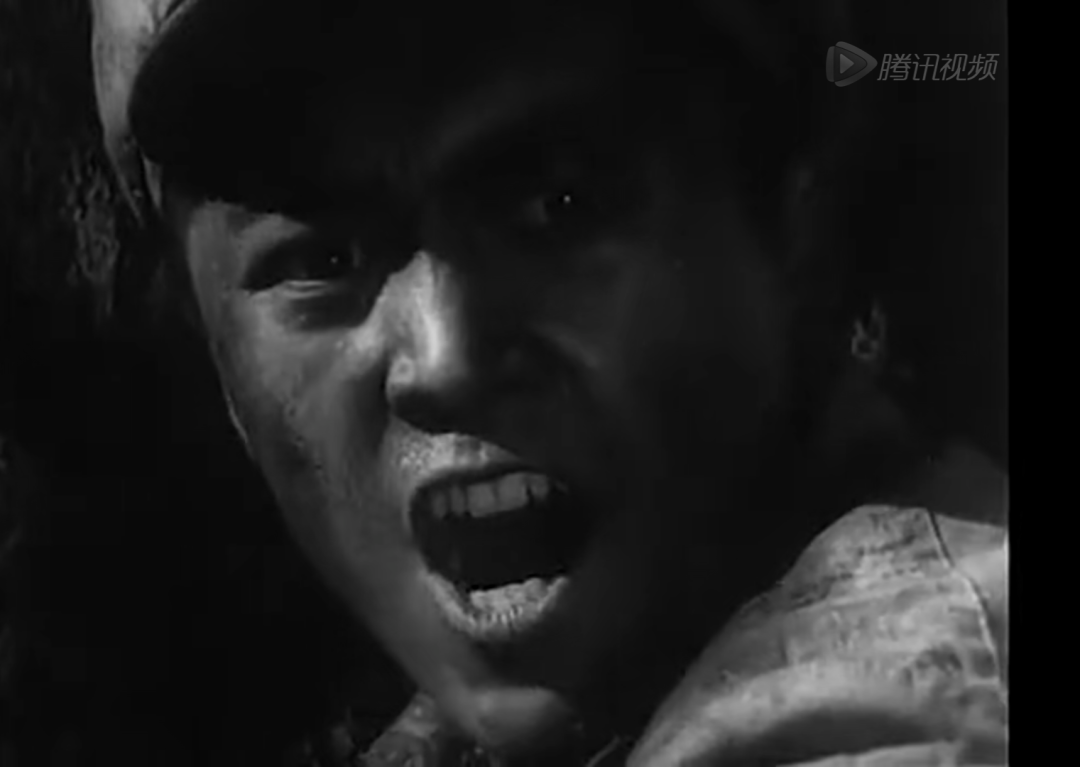
電影《上甘嶺》
為了貼近真實,導演還請了參加過上甘嶺戰斗的戰士來當軍事顧問,其中有堅守坑道14個晝夜,帶領連隊打退敵人幾十次進攻的趙毛臣。但是影片上映后,很多一起在坑道蹲過的戰友都問他,“你那個坑道就這個樣兒?你就沒有把那個真實情況拍出來啊!”
電影里,缺水少糧的戰士們在坑道里打牌、下棋、與突然闖入的松鼠嬉戲,而實際情況是,幾十乃至上百個戰士在坑道里人挨人地站著,還要給傷病員留出半躺的空間,由于排泄物污染了水源,長時間沒有水喝,每個人渴到張開嘴貼著四周涼石頭才能稍微緩解的程度,最后只能喝自己的尿。

電影《上甘嶺》拍攝現場
所以,凡是參加過上甘嶺的戰士都說,這個電影離戰爭太遠了。可這正是導演沙蒙的堅持,他刻意回避了真實的坑道和近戰肉搏的情節,他對不理解的演員說,“我就是要表現和平,不能給觀眾刺激的鏡頭,要給他最美好的鏡頭,這樣觀眾才能記住你,回憶你。”
電影拍完,導演沒有讓攝制組解散,他說這樣一部戰爭片,中間一定要有一首插曲。

一條大河
被請來寫插曲的是28歲的詞作家喬羽和34歲的作曲家劉熾,從南昌趕到長春的喬羽被拍好的片子打動,但也犯了難,他和劉熾上一次合作的歌曲是為孩子們寫的《讓我們蕩起雙槳》,這回面對上甘嶺那么慘烈的戰斗,他不知從哪下筆。
喬羽憋了好幾天寫不出一個字,他一度想放棄,因為整個攝制組停工待料地等他,每天的成本就有三千塊,導演沙蒙天天都到他的屋里,也不多說話,坐一會兒就走。
有一天喬羽實在頂不住了,對導演說,“沙蒙同志啊,你對這個歌有什么要求?你覺得該怎么寫?”沙蒙說沒要求,你愛怎么寫怎么寫,喬羽堅持讓他說個要求,沙蒙說,“我的電影將來沒人看了,你的歌照樣有人唱,我就要這樣的歌。”
喬羽正苦惱的時候突然天降大雨,雨后他走到小河邊看到一群孩子們歡笑奔跑,腦子里馬上涌出一句,“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困擾他兩個星期的歌詞幾分鐘就寫完了,沙蒙拿著詞反復看了半天,說了句,“就它了”。
第二天,沙蒙又來了,說“一條大河”是長江嗎,喬羽點頭,那為什么不寫“萬里長江波浪寬呢”?喬羽說,“不管你是哪里的人,家門口總有一條河,一個人一輩子都忘不了家鄉的那條河,不要說是哪條河,就一條大河吧。”

歌詞通過了,犯愁的人換成了劉熾,那幾天他在大半夜高聲地唱各種歌,吵得別人沒法睡覺,他還讓同屋的演員張亮給他朗誦喬羽寫的詞,折騰了半個月,《我的祖國》終于完成了。
演唱這首歌的郭蘭英當時才二十幾歲,她問領導,開頭的一條大河是哪條河,領導也沒想過這個問題,隨口說,“就你們山西那條河吧。”郭蘭英再問山西的哪條河,領導有點不耐煩,你想哪條就是哪條,錄音的時候,郭蘭英心中想的是母親河黃河。
在影片中唱起《我的祖國》的角色是衛生員王蘭,她的原型叫王清珍,參加上甘嶺戰役時還不到16歲,一個人在山下護理二十多個傷員,每頓都吃傷員們的剩飯,如果沒剩下來,她們衛生員就餓一頓。

當時有一位傷員需要鋸掉腿,看她年紀小,就問她怕不怕,王清珍說,“你們不怕,我也不怕!”這位戰士很樂觀,忍著痛對她說,“給我唱首歌吧。”王清珍帶著口罩不方便唱,但一想到傷員的痛苦,就一邊包扎一邊哼起了陜北民歌《南泥灣》。
導演給志愿軍戰士們讀劇本的時候,他們強烈要求把衛生員的情節安排到坑道里,要不然他們就不參加群演,這背后是多年來難以言說的故事,當年很多傷員無法小便,需要插導尿管,后來導尿管也不夠用了,看著快憋死的傷員,男女衛生員就選擇用嘴處理,那時他們都是十幾歲的小伙子小姑娘,其后幾十年再也沒人提起過。
1952年11月25日,上甘嶺戰役結束,志愿軍失去兩個前沿班陣地,堅守住了大部分高地。四年后,導演沙蒙帶著攝制組在北京拍攝了《上甘嶺》的最后一場戲,他們在西山上找了一棵大松樹,拍完了放生松鼠的鏡頭。
《我的祖國》 (《上甘嶺》電影主題曲 郭蘭英 演唱)

向我開炮
在上甘嶺戰役結束的1952年冬天,作家巴金到了朝鮮,他在采訪中聽到了一個動人的故事,失散多年的父女在朝鮮戰場重逢了,父親叫王文清是政治部主任,女兒叫王芳是部隊的宣傳干事。
1961年,巴金把這個故事寫成小說發表在《上海文學》上,取名《團圓》。兩年后,導演武兆堤把它搬上銀幕,他出生在美國匹茲堡,五歲跟父母回到中國,十九歲那年去延安當了文藝兵,拍《英雄兒女》之前,他已經和蘇里聯合執導了著名電影《平原游擊隊》。
在原著里,巴金對王芳哥哥王成的描寫只有一句話,“這個團完成了上級給的任務,友軍也終于趕到了。只是王成沒有能回來。他勇敢地在山頭犧牲了。”
武兆堤對編劇毛烽說,“你在朝鮮戰場待了三年,把王成這個人物‘立’起來。”于是就有了“為了勝利,向我開炮”的經典一幕。

電影《英雄兒女》
王成的形象來自多位戰斗英雄,有抱起炸藥包跟敵人同歸于盡的楊根思,但他沒有說過“向我開炮”的話,武兆堤和毛烽是在戰地記者洪爐的一篇報道里發現了說過“向我開炮”的兩個原型,蔣慶泉和于樹昌。
這兩人都是部隊的步話機員,肩負指引炮兵打擊敵人的任務。據蔣慶泉回憶,那次任務他們連只剩了十幾個人,最后退到碉堡里,他想沖出去拼命,被戰友攔了下來,讓他呼叫炮火。
50米、30米、10米,敵人越來越近,最后蔣慶泉向步話機喊,“向我的碉堡頂開炮!我們不撤了,就戰死在這吧。”
蔣慶泉沒有戰死,他讓炮彈震暈后被敵人俘虜。陣地丟了,這次戰斗也被暫緩宣傳。他的戰友聽見了那句著名的“向我開炮”,并迅速在軍中流傳。
兩個月后,在另一個山頭傳來了同樣的聲音,這位步話機員就是于樹昌,那次戰役成功阻擋住敵人最后一次猛烈進攻,不久后朝鮮停戰協議簽定,于樹昌的名字也開始在全國傳播。
挑選王成的演員時,武兆堤力排眾議地選擇了個頭不高、形象普通的劉世龍,他看重的是這個小伙子的當兵史。劉世龍9歲就跟著父親、姐姐參加新四軍,從小就在文工團長大,49年還在四川、貴州剿匪一年多,是經歷過生死考驗的老兵。
解放后,劉世龍被選送到北京電影學院,扮演過《董存瑞》里的通訊員,看了《英雄兒女》劇本,雖然“王成”在影片開始17分鐘就犧牲了,但劉世龍做夢都想演好,為此他到部隊體驗生活,三四個月時間曬得黝黑。
和他一起下部隊的還有在《平原游擊隊》扮演“游擊隊長”李向陽的郭振清,他在《英雄兒女》演團長,劉世龍說,“大郭是直爽的軍人氣質,說話隨意,不拘小節,做事認真。”

郭振清
電影的外景地選在沈陽至丹東的路上,那邊有像朝鮮的山形,本來打算去朝鮮拍,但聽拍過《上甘嶺》的人說,他們當年被“黑”了五倍的費用,就沒再去。
王成犧牲的陣地是在本溪南芬找到的,那是一片老鄉的高粱地,劇組把地炸了一遍,挖戰壕、修工事、埋了108個炸點。實拍的時候,劉世龍端著十幾斤重的蘇式機槍在火海中穿越,他剛跑起來就想喊停,但想到眉毛和臉燒著了也死不了,就豁出去干了。
雖然炸點很多,但“向我開炮”那場戲一次就過了,回去的時候,劉世龍一身黑灰,臉上有灼燒的痕跡,頭發、眉毛都有燒焦的地方,軍裝也燒出幾個大洞,他不想弄臟劇組的車,就爬上道具車返回招待所。
電影上映后,劉世龍的“王成”成為那個年代的英雄化身,在朝鮮戰場上,有太多和他一樣其貌不揚的小個子戰士,就像影片插曲《英雄贊歌》里的那段朗誦,“在中國人民志愿軍里,有千千萬萬個王成”。
為了抒發更多人對英雄的崇敬,《英雄兒女》也同樣需要一首插曲,可是武兆堤和毛烽寫來寫去,只有“中國人民志氣豪,抗美援朝英雄多”這樣的詞,倆人果斷停止了“創作”,和負責作曲的劉熾去拜訪吉林大學中文系主任公木,他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和《東方紅》的詞作者。
當時處于運動旋渦的公木擔心寫了也用不上,但三個人反復勸說,公木就想以最快速度寫完,好盡快打發他們走。結果一晚上就寫出來了,《英雄贊歌》就這樣誕生了。

在只有樣板戲高亢激昂的年代,《英雄贊歌》顯得格外抒情和動聽,在電影里唱響它的是文工團員王芳,她的扮演者劉尚嫻是武兆堤委托謝晉導演在電影學院找到的,當時她剛畢業。在朝鮮戰場,十幾歲的文工團員們在戰火穿行中長大,鼓舞了戰士們,有一些人永遠地留在了那里。
1994年12月,劉世龍、劉尚嫻一塊兒到醫院探望病重的巴金。看到自己筆下的“王成”“王芳”兄妹,巴金揮著雙手不停招呼。劉世龍含著眼淚貼著巴金的耳朵說,“巴老,我是王成。”他還說了電影中的臺詞,“為了勝利,向我開炮。”劉尚嫻也說:“我是王芳。”
巴金緩緩地說,“《英雄兒女》拍得好,我很喜歡,我看過好幾遍。我沒有把作品寫好,是電影改編得好,導演導得好,你們演得好。我只是提供一個故事,電影把它的內容豐富了。”

遇水架橋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沒有商業大片,《上甘嶺》《英雄兒女》里的美國兵都是戰士們貼著紙殼做的假鼻子演的,但演員手里的武器都是真槍,有一回越南電影代表團來長影參觀,看到道具倉庫分門別類的武器,感到很驚訝。
一晃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我們等來了第一部抗美援朝題材的戰爭大片《金剛川》,在朝鮮戰爭最后階段的金城戰役中,為了守住一座至關重要的橋,志愿軍同美軍展開了生死較量。

電影《金剛川》
影片結尾,再次響起了《我的祖國》和《英雄贊歌》的旋律,在金剛川那座用生命筑起的浮橋上,完成了對一條大河和向我開炮最激昂與深情的致敬。
《英雄贊歌》(《金剛川》電影主題曲)
責任編輯:單蓓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