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茅盾文學獎得主張煒再推新書,一本是他目前唯一的長篇非虛構作品《我的原野盛宴》,一本是他延續自身詩學研究的《斑斕志》。兩本書的付梓為國內出版業帶來諸多看點,吸引了眾多關注目光。昨天下午,張煒做客青島書城一樓城市課堂,與讀者對談、分享創作中的心得與心路。這兩本新書的作品類型、語言風格、整體風貌大相徑庭,這也從側面映照出作者對“我手寫我心”的文字駕馭能力、對生活經驗的打撈重塑能力以及對往圣先賢“通古今之變”的思辨能力。

《我的原野盛宴》解讀非虛構
張煒的文學創作多產且多樣,《古船》以來,他的小說作品蔚為大觀,既有鴻篇巨制 《你在高原》,也有為青少年而作的《尋找魚王》,還有《九月寓言》《刺猬歌》《獨藥師》等種種。這些作品或是現實主義小說,或是余味悠遠的寓言小品;有的被譽為巔峰之作,有的贏得文學大獎,都一再標定著作者在現當代文學史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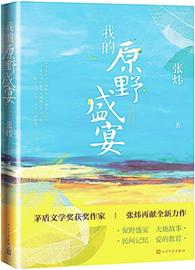
《我的原野盛宴》是張煒在小說之河上豎起的一張獨具風格的船帆。這部小說描繪了360多種動植物,堪稱一部膠東半島動植物志。在35個故事段落中,他寫下了一個人的成長史和心靈史,完成了 “記錄一個時代,復活一段歲月”的工作。有評論家說,《我的原野盛宴》續接了悠遠的“國風”,從書中可以感受到《詩經》《山海經》的悠遠氣息。
在張煒看來,《我的原野盛宴》是一部非虛構作品,與小說還有不同。 “每一次面對千瘡百孔、目不忍睹的東部半島海濱平原,就有一種撕痛感。關于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回憶常常纏住我,讓我耿耿難眠。記錄過去的生活、過去的海邊林野,成為一種責任。這種記錄一定是重要的。 ”
《我的原野盛宴》是張煒第一次書寫較長的非虛構文字,也是張煒所認為的在目前時間向度上個人最滿意的作品。張煒表示,對于寫作者來說都有這樣一個經驗,虛構固然很困難,但也更自由,“非虛構的寫作就要寫真實的經歷,每一點都得非常小心,其中有個人的禁忌,還有許多私人化的東西需要處理,不能泥沙俱下,同時在寫作過程中還需要文學的高度、語言的高度等許多要求,將其和諧統一地處理在一本書里,需要相當多的人生經驗和文字歷練。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的原野盛宴》對我很重要,我也很看重,它在我一生的自傳文本中也是很重要的一筆。這大概也是我在走過40多年文學之路后,才有的一種自信、一種從容、一種筆力,再早一些可能沒有力量去駕馭。 ”
《斑斕志》還原蘇東坡
與非虛構的《我的原野盛宴》不同,《斑斕志》則是以今日作家眼光關照昨日圣人文章,全書由超過10萬字的講義、30多小時的講座錄音、20多萬字的初稿整理而成,最終形成“苦思別悟,不落套語解東坡”的新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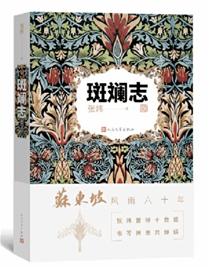
《斑斕志》最初名為《蘇東坡七講》,而《斑斕志》則是其中一個篇章的名字。談及該書的出版原因,張煒直言這不過是他在刻意尋求中國傳統詩與現代自由詩的焊接過程中的“副產品”。
“我酷愛寫詩,但詩對我而言是一個難題,一方面可能是我愚笨,另一方面是寫詩太難了。 ”張煒直言不諱,中國的現代自由詩要走得更遠,不能回避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跟中國詩的傳統接起來,“我曾有過一個比喻,二者就像是木頭和鋼筋無法焊接到一起,中國的律詩、詞、古風,跟今天西方意義上的現代自由詩歌有著不可能拼接的關系。這個難題很大,大家做不好,我也做不好,所以我便下了很大的決心,把中國有代表性的詩人及其作品,以及有關他們的文字,都讀了一遍。不夸張地說,我積累的有關蘇東坡的相關資料摞起來可能比我個頭都要高。 ”張煒做了20多年中國古詩學的研究,其中心只有一個:“圍繞著怎樣能夠寫好現代自由詩。 ”
具體到蘇東坡,《斑斕志》的目的意在還原。對于許多人來說,蘇東坡是最為熟悉的詩人之一,為坊間提供的談資特別多,但在張煒看來,如此通俗化的過程中也存在著一個問題,“通俗化是好的,讓底層的老百姓都知道他,但缺點就是在這個過程中難免會被庸俗化。一談到蘇東坡,大家可能津津樂道于他很有女人緣、很有才氣,天性浪漫,卻又遭遇不幸……但這只是表面,深入研究之后你會發現,他可太復雜了。任何通俗化的過程會丟掉很多東西,損失是巨大的。所以對于蘇東坡,我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他在通俗化的過程中損失掉的、歪曲掉的部分打撈、糾正、更改。 ”而張煒在這個過程中秉持著一個自我的原則,將《斑斕志》定位于傳記,而非傳記小說,摒棄一切虛構與想象,“事實和行跡盡可能地還原;思想和藝術盡可能地貼近;另外加上個人化的表達,將我長期以來對事物的判斷和審美特質融入其中,一定是不落窠臼地呈現。 ”
[作家觀點]
哪有什么“當代經典”
除了《我的原野盛宴》和《斑斕志》這兩本新作,張煒還于前不久出版了一部長詩作品 《不踐約書》,不到4個月就再版了12000冊。但張煒早已不再過分關注銷量和市場,“如果各種宣傳銷售手段都用上,達到一二百萬冊的銷量,而作品本身卻令人不敢恭維,這又有何用呢? ”
張煒直言,文學和藝術不是以讀者多少來決定品質的,“藝術沒法在有限的時間里去迎合讀者,讀者和民眾是一個時間的概念,而不是具體的可觸摸的銷量。 ”在解讀這等文壇現象時,張煒坦言,如今經常會有人說當代經典如何如何,“當代怎么會有經典呢?所謂經典,一定是時間和典范的意思——經歷時間,足以成為范例。經典必須經歷足夠的時間,起碼是百年的檢驗,如果面世不過一二十年就說是經典,那就太可笑了。我的書寫得到底好不好?我的藝術到底有沒有價值?光靠自信不行,光看銷量也不行,這一切都只是一個微小的當代參考。 ”張煒表示,所謂的藝術和思想,不是當代人近距離能夠看得清的,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堅持真理,熱愛文學、敬業,將全部力量用在 “純粹”這兩個字上,“搞藝術、搞文學,最終比的就是誰更純粹,而不是比誰更江湖。 ”(觀海新聞/青島早報記者 周潔)
責任編輯:單蓓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