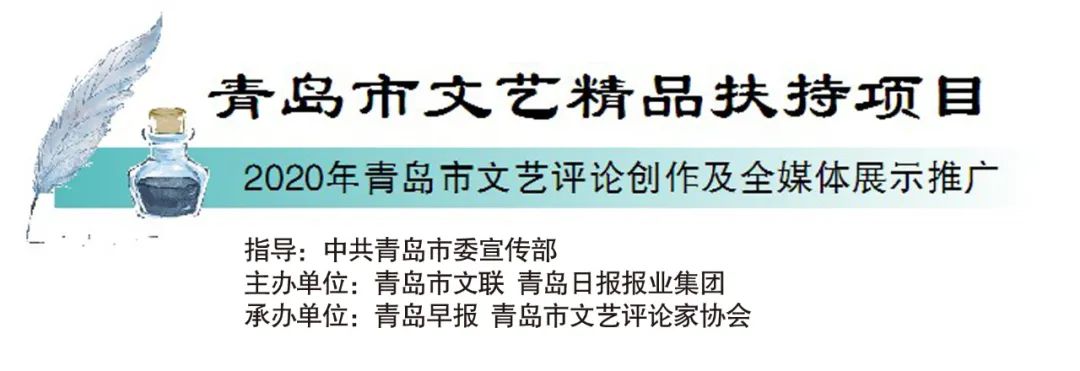
一條魚飛到天上,碰到了一只鳥
作者:陳為朋
因為這個令人驚詫的句子,我決定寫這篇短文。
喜歡魚和鳥兒的人,都有一顆自由的心。自由是最可珍貴的,來自于生命的意志,像鳥,每一片羽毛都閃著自由的光輝;像魚,即便只有鱗片也要奮力一躍,如鳥兒一樣飛翔。
有的人做任何事,都會讓人驚詫,比如阿占。她從去年開始寫小說,第一篇《制琴記》被許多名刊轉載,幾乎同一個時間段,她的散文集又獲泰山文學獎。但我似乎覺得也正常,因為這是阿占。
“一條魚飛到天上,碰到了一只鳥”這個句子,就在她另一篇兩萬五千多字的中篇小說《滿載的故事》里。小說寫的是胡家林漁村村民滿載的一生。
二十多年前,我與阿占同在《青島晚報》副刊部工作。她當時主編《島城山語》專欄,為了寫山,她把青島的山走遍了。也許在這些起伏的山脊上,她遇到了那只羽毛上閃光的鳥兒。之后,她又寫了一個海的系列《多情海岸》,也許在這片無垠的蔚藍里,她遇到了那只要飛離海面的魚兒。同時,她成了一個“比漁民更像漁民”的寫作者。寫完山與海,我們又策劃了“人系列”《青島世家》。后因版面調整,此事作罷。
但阿占沒有作罷——她想做的事好像就沒有作罷過。她把遇到的俗人奇事寫成了九本書,其中一本叫《青島藍調》。她說她喜歡藍色,更喜歡黑白:“小說即黑白。”
阿占自小學畫畫,在她的書里,大量插圖都是自己畫的。她說:“我希望我的畫里,街道更像河床,飛鳥根本就是懷孕失重的魚——統統一切都在意識里——小說亦如此,《滿載的故事》里的滿載,這個生下來就是一個天才的‘職業漁民’,也像一條失重的魚,但他也要飛到天上,雖然他并不知道為何要飛。”

這部中篇我讀了三遍。
第一遍是初稿。海明威說“所有的作品初稿都是垃圾”,我不完全同意這句話,但還是給阿占的小說寫了兩點意見,是她讓我寫的。
第二遍是刊出之后,我讀到了那條魚和那只鳥兒,還有一個人的一生:“老了的滿載,沒有人知道他真正經歷過什么。時間顯示出不動聲色的力量,流沙的軟金覆蓋了所有的秘密。”人生的秘密,不動聲色的時間,自由的意志,如深不可測的海底,阿占如何知道?又如何做此精準而又傳神的描述?
作家余華說,美國作家辛格的《傻瓜吉姆佩爾》和巴西作家羅薩的《河的第三條岸》異曲同工,都是由時間創造出了敘述,讓時間幫助一個人的一生在幾千字的篇幅里栩栩如生。意思是他的《活著》里的福貴,也是這個樣的“栩栩如生”著。你是不是覺著,我的意思是說,阿占的小說里中的滿載,也是如此“栩栩如生”呢?幾千字能做到,兩萬多字也能做到吧?
第三遍是寫這篇短文之前,我把這部中篇認認真真讀了一個多小時。我發現了另一個秘密,我一直在想的關于寫作的“秘密”。詩人里爾克說羅丹的雕塑: “在人體的表面上取得了進展,這表面是由光和物的無數次碰撞構成的。這個大小不同、色調不一、精確規定的表面,用它可以創造一切。”
小說的寫作也有“表面”,那就是“詞與句子”。阿占小說里讓人驚詫的句子比比皆是。
寫人的悲傷:“一張張臉上套印著悲戚,村前村后地走,把白日走黑了,又把黑夜走白了。寬慰的話一旦出口,就蒼白無力起來,他們只能吞咽下去。”
寫器物之精準:“不銹鋼的刃身,經過了精湛的石洗工藝處理,以凹磨手法開刃,獲得了最大的鋒利,切割能力異常出色。回形刃頭,可以更好地進行切削,是最具穿透力的一種形式。刃背后端的滾花凹口,讓使用者能更精確有力地操作……”
寫人的潛意識:“垂死的魚,在黑暗中流血,抽搐,最后又無一例外地變成了嬰兒。偶有一條倔強不甘,背脊上長著半圓的黑斑,忽然首尾支撐,像拱橋那樣彎起身子,豎起無望的前鰭,但也用不了多久,它回到死刑中,變成了一個男嬰。”
人類與自然的關系,是一種依附與征服的博弈。而滿載所要表達的,除了一個人對命運的不甘,還有面對大海時命運的那種無常;還有,寫了一個人精神上的成長。
《滿載的故事》多了又一個主題,即倫理道德間的博弈。以滿載為一方,以船老板胡老大為另一方。受拜金主義影響,“胡家林的人變壞了。變得冷漠、癲狂、狡猾。養殖濫用抗生素和激素,捕撈用絕戶網……作孽呀,違背自然規律,要遭天譴的。可沒過幾天,人們就發現不用不行啊,你不這樣做,讓別人做了去,錢就不再找你”,用這樣的一種描述,阿占表達了她對時代的某種思考,也顯現出她對未來的某種焦慮。
這樣的雙主題,從好的一面講,作品變得豐富厚重;從不太好的一面講,對作品的純粹是種傷害。到底是哪一方面,取決于你從什么視角去看。
而我看到的,更多的是阿占的才情,一種掩飾不住的才情。二十多年前她寫山,寫海,寫青島的人間百態時,這種才情就已存在。
現在,阿占多會住在海對面的小珠山中,那兒有很多的鳥;回到她在八大峽的家里,她會下海游泳,海里有很多的魚。她是不是也想變成一條魚兒,然后飛上天,變成那只羽毛上閃著光輝的鳥兒。那是一個人的自由意志。她把她的這種意志賦予了“滿載”,使得這個人物有了藝術價值,有了值得你一讀的理由。
(作者簡介:陳為朋,作家、資深報人,創作有小說、散文和影視劇本等作品。)

責任編輯:單蓓蓓



